張冬芳
〈悲哀──贈張國雄君之在天之靈魂〉 在草原上摘紅花, 去菜園裡刈些青草, 啊!我的眼淚哭乾了, 你的靈魂已經杳杳不知到那裡, 我可憐的不是你一個人 今天的報紙十四匪謀的地方, 馬場町的青草, 他們己開始用血洗了, 〈一個犧牲──被強徵到南洋死去的一個朋友〉 他是我的好朋友 ……譬如……被美機炸死 南海的波瀾這樣大 你在天之靈 在靈桌上的相片 〈對話〉
用鑽子鑽在心臟上,
將血任其流在面盆裡
來給你洗臉。
編成一個全紅的花環
來給你套上。
做了些青草湯
來給你供拜。
啊!我的聲音也啞了,
我並沒有什麼可向你餞別了。
那是表示你已在樂園了。
短短三十的人生,
你也有留下兩個女孩。
可憐的是你的妻人,
那麼年青要叫她如何
老母還有弟弟奉養。
可憐的是台灣的人材
將被消滅了。
我有些不敢近視了,
每天都有熟人,
使我惻惻悲哀。
吃了台灣人高貴的血
一定是長得很好吧。
好吧!睜開眼睛看看
血價什麼人要償哪!
──1950年代
想起來也是一件傷心的事
去年的冬天
淒晴的一日
你說給我听
──死!我是不怕,怕狗似死的
又是一個仁慈的醫生
他的磊落是我的欽佩
……祖國能勝利……我也
甘願……
你告別的一言
孤島的生活這麼無聊
一隻絕望的小貨輪船
載了像奴隸似的你們
開了西貢的港口了
太陽剛從水平線上
剛露出她紅紅的臉
黑暗初除,怯弱軟和的光線
照出了焦瘦的黑臉
在船艙上三三五五
享受早晨自由的空氣
誰能預料到……
F˙6˙F一架飛到
一剎那頃
機關鎗響了
炸彈的恐怖的怒吼
叫天不應喚地無聲
真是一剎那頃
海面上只剩下一個大波紋
遙遙來看我們的光復
好像一場的大夢
你死啊?
你家裡……老父老母
等著不能回來的你
剛結婚的新娘抱著嬰兒泣哭
是你的唯一的寶貝
你又不知道他的存在了
還在洩露那個諷刺似的微笑
你是不是?
在笑壓迫者的最後嗎?
──《政經報》1卷5號,1945年12月25日
紅豆仔冰,紅豆仔冰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紅豆仔冰……
倒霉 倒霉 沒有人買
喂!你賣幾枝了
沒有!?
噢 秋風這麼冷
喂!來來!你看看
看什麼 有什麼好看
鬼獅 人家在吃飯
喂!在吃乾飯的!
有什麼希罕呢! 肚子餓起來了
回家去 吃稀飯吧
倒霉 做賠本生意
不要回去了 紅豆仔冰 紅豆仔冰
怎麼? 怕媽媽打麼?
噢! 秋風怎麼這麼冷。
──《新新》第2卷第1期(新年號),1947年1月5日
§作者簡介§
張冬芳(1917-1968),台中豐原人。豐原公學校畢業,爾後入台中一中就讀,考入台北高校。在台完成高中學業後,旋即至日本東京帝大攻讀中國哲學系。返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中文系。與作家呂赫若同為鄰居,往來過從甚密。白色恐怖期間,呂赫若逃亡至深山,傳聞被毒蛇咬死,張冬芳則避居豐原老家,四處流離寄居於親友、佃農家中甚至墳場,終至倖免於難。五0年代後返台中豐原,遂棄文從商,不再提筆。張冬芳的詩作批判嚴厲,直抒時局暴政,多描寫個人及友人的流亡經驗。發表於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個月左右的〈對話〉,以白描口語的方式鋪陳出寒風中賣紅豆仔冰的小市民辛酸,語言生動,毫不雕琢,生動而直接地再現了事件前夕台灣社會普遍窮困貧乏的景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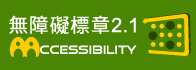
![我的E政府 [另開新視窗]](/images/egov.png)
